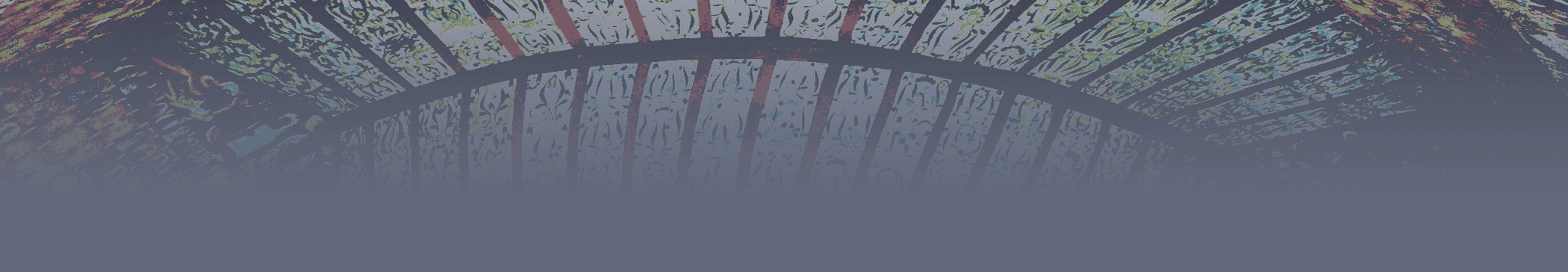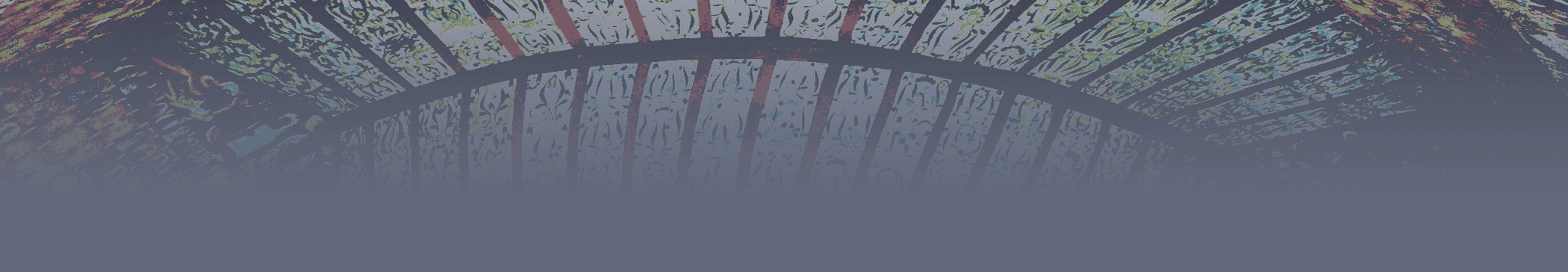| |
| |
| 千年瑰宝的守望—听“敦煌的女儿”讲述莫高故事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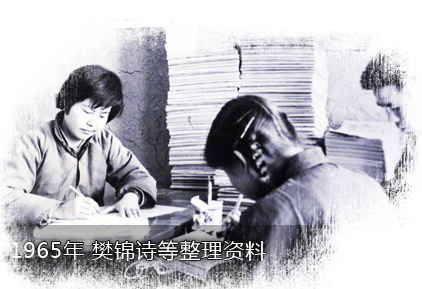 从此,常书鸿便将一生心血献给了敦煌。“飞天漫舞洗尘殇,饲虎舍身宣教义。万里黄沙着意量,一生心血寄敦煌。” 这首诗诠释了他的一生。 从此,常书鸿便将一生心血献给了敦煌。“飞天漫舞洗尘殇,饲虎舍身宣教义。万里黄沙着意量,一生心血寄敦煌。” 这首诗诠释了他的一生。
而提起“敦煌艺术导师”段文杰,樊锦诗也有说不尽的话。“段先生经常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,小樊啊,你不要走啊。”樊锦诗回忆,段文杰退休了以后依然对敦煌念念不忘。孩子把他接到兰州,有一次半夜睡觉,他竟在梦里嚷嚷着说“你们怎么还睡觉,还不起来上班”。
1944年,在重庆国立艺专上学的段文杰,因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。就“着了魔”,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心中的艺术殿堂,此去就是一生。“段先生身上真正体现了‘打不走的莫高窟人’的那种精神”。——的确,敦煌像一块磁铁,吸引着钢铁般的人们。
作为“敦煌的女儿”,樊锦诗又何尝不是呢?
1966年,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结婚,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,分隔千里,两人只好鸿雁传书,遥寄相思。作为一个妻子,一个母亲,她抛家离舍,独自一人在敦煌整整工作了19年。1986年,彭金章最终妥协了,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,来到了敦煌。樊锦诗说:“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”。
像樊锦诗和彭金章这样的故事,在敦煌绝不是孤例,更不在少数。在采访过程中,樊锦诗多次说:“你们不要拍我了,不要写我了,我樊锦诗的镜头太多了,你们要多报道其他人。”
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,有一处矮矮的沙丘。沙丘之上,坐东朝西,与莫高窟九层楼相对,有22座墓碑。墓碑上镌刻着敦煌研究院已故老同志的名字与生卒年,常书鸿、段文杰也埋葬在这里。
岁月倏忽而逝,相对于千年敦煌,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。然而,在短暂的生命间,这些茫茫大漠之中,艰难苦辛、筚路蓝缕的敦煌人,却留下了最美的光芒。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,最后埋骨沙丘,面对万佛圣地,他们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。(完) |
|
|